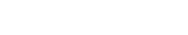


在云南省红河州的滇南小城石屏县,生活着一支岳飞的后嗣。相传,其代代运营一项名为“乌铜走银”的传统手工。2011年,乌铜走银制造技艺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北京“景泰蓝”齐名,并称“全国铜艺双绝”。
乌铜走银制造技艺主要有“两奇”,先说最要害的“走银”。匠人用火熔化固态银或金,经过精准操控不同金属的熔点临界值来完成“走银”,让银水跟从手中的动作流进錾刻好的细沟密纹中。在操作上考究“快准稳狠”,铜的熔点为1084℃,银的熔点为960℃,这要求匠人只是凭仗阅历、感觉来把握一百来度的火候差值,温度过高会让银与乌铜糊作一团而前功尽弃,过低则无法将银水充沛走入图画中,只能生成残次品。
再说“捂黑”,乌铜走银是用优质的紫铜和特别的份额的金、银等十余种贵金属交融锻炼而成的合金,成型后的乌铜走银通体呈淡红色,需求用手掌重复摩挲,让汗液与乌铜合金充沛产生“氧化复原”的化学反应,乌铜器才会变得漆黑亮丽。人体酸碱阈值的不同,会让包浆后的“漆黑”深浅纷歧,终究呈现的颜色独具个人特性。鉴于此,乌铜走银也被称为“最有生命力的金属”。
成器后的乌铜走银黑底白章、厚重高雅,錾刻形似我国画的白描方法,花鸟鱼虫、飞禽瑞兽、吉利纹样、文人书画等纹饰图画跃于方寸器表之间,意韵悠长、独一无二。
相传,乌铜走银为岳飞后人创始,石屏的岳姓铜匠偶尔锻炼出一种能使铜器发亮发黑的合金,后逐步改善配方、加以装修,才构成乌铜走银。为了独家运营,锻炼乌铜的秘方概不别传,代代遵从“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祖训。
岳飞后嗣、独门诀窍、传奇源起,这一些要素似乎为乌铜走银蒙上一层奥秘面纱,若要拨开笼罩在它身上的重重迷雾,会牵引出一段又一段杂乱的前史。
岳飞后嗣入滇,最早可追溯到明洪武年间。朱元璋为处理云南长时间割据的现状,发起了前史上闻名的“调北征南战役”,派沐英等人征滇。战势安稳后,明朝又连续差遣戎行在云南构成军事屯堡,推广“就宽乡”移民方针,鼓舞人口稠密的江南、江西一带的人口迁徙到云南。这与《石屏县志》所记载的“石屏明初复添石屏、宝秀二屯,屯军皆江南北人”根本共同。
石屏岳家湾的岳氏先祖就在此关键下进入石屏。据通海《岳氏宗谱》记载,岳飞后嗣岳宗礼,在沐英征滇的布景下从湖南衡阳迁徙到云南通海,成为通海岳家营的一世祖。通海与石屏相邻,通海岳家长房的分支三人一起到石屏冒合山脚久居,后逐步开展为岳家湾。石屏《岳氏家谱》记载“二十四世祖在此久居后,后代旺盛兴旺,祖传手工艺乌铜走银”。
可见,乌铜走银技艺确为岳飞后人代代传承,但该技艺是否为岳家创始、创始,乃至是否发源于清雍正年间,又呈现了不同的声响。
学者李朝春考证史料后发现,遍及撒播的乌铜走银“起源于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这一说法最早呈现在1977版的《红河州志》,后广泛被当地文献选用,但此为孤证,很难立得住脚。
原因有三,一是乌铜本是我国传统金属铜合金之一,早在宋代文献中就有相关记载,明代也大量呈现乌铜器物。石屏乌铜走银工艺很可能是在我国传统铜工艺基础上开展起来的精品铜艺术,直至清代,内地也在大批量出产和运用乌铜器,石屏乌铜器并非个例和当地仅有。
二是清末从前,云南相关志书均没有乌铜走银源于石屏、源于清雍正年间或“某某发明”“首制”之类的说法,只要“乌铜器制于石屏”“始惟岳姓能制”“岳家湾产者最佳”等寥寥数语。
三是民国时期“岳福兴号”乌铜店主人岳祯祥注销的一则广告可构成佐证,“昔在岳家远祖随沐英征滇,卜居石屏,得异人教授秘方,用金银铜铁锡并参加最可名贵之药料炼制以成乌铜,凡日用必需之器皿皆可制造”。
根据上述依据,乌铜走银的身世之谜才被逐渐揭开:乌铜走银技艺确为岳飞后人所把握,并代代运营。在云南这片盛产贵金属的膏腴之地,岳飞后人依托当地商帮的活动取得稀有的宝贵金属,并在“异人教授秘方”的基础上不停地改善改造配方、精深技艺,让石屏乌铜走银成为别出心裁的存在。
乌铜走银的开展深度嵌入云南当地与我国前史,在清末民初这一风云际变、民族动乱的特别时期,曾以双面形象兴起,既是瘾君子的“烟膏盒”,也是文人雅士的“墨盒”。
战役后,上至达官高贵、巨贾大贾,下至市井小民、贩夫走卒,啃咬的习尚以瘟疫之势敏捷苛虐全国。云南更因边地步形和土地肥美而“遍种罂粟,熬膏售卖”。一时之间,各种烟枪用具数量如炬,上层阶层更是豪掷千金寻求烟具的豪华与高雅,为烟枪镶金嵌玉、装点珠宝,以示身份显贵。
对这一巨大商场,石屏乌铜走银匠人们纷繁开端仿照内地烟具款式制造烟器,既有工艺精深的烟枪,也有形制精巧的烟膏盒,因而,烟器也成为乌铜走银现存世量最多的器型之一。
俗称大烟、福寿膏,烟膏盒是贮存的容器。常见的乌铜走银烟膏盒有圆柱形、腰子形或椭圆柱形,也有四方柱和六方柱形。就算用来装烟膏,匠人也尽头技艺,在盖面、底面走金或走银,勾勒山中隐寺、远山近景、山清水秀,营建奔放空灵的意境。
烟枪是用来啃咬大烟的东西,比较造型单一的烟膏盒,烟枪的用料更为奢华,装修上也更杂乱精美。枪杆通体或部分走金走银,烟嘴、堵子、斗子一般用温润的翡翠、紫陶或象牙。
当然,这一段“黑前史”绝非乌铜走银所仅有,随意翻开此间史书的一页,就会发现,从金银漆器到陶瓷玉石,制造烟具受时代所驱,不是匠人的自在毅力所能决议的。
而制造墨盒,也与其时盛行的风潮有关。晚清时期,砚台离场,墨盒盛行,铜墨盒成为文人雅士们的新宠。民国后期岳家制造的乌铜走银墨盒可与京津一带盛行的刻铜墨盒相媲美,占有我国文玩墨盒的半壁河山。乌铜走银墨盒以方、圆为主,精巧高雅,常见梅兰竹菊四君子纹样,也有名家书画、山水风光等。
1916年,“岳记福兴乌铜庄”岳应制造的乌铜走银工艺品取得了昆明花朝会乙等奖,一时之间,乌铜走银名声大噪,成为政商名人争相追捧的赠礼上品。
龙云执政云南期间,历年都要到岳家定制一批乌铜走银的墨盒,落上“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赠”的字样,给蒋介石备做人情之礼。蒋介石送给黄埔军校优异毕业生的墨盒上便有刻文“设笑定东北,勋名建蜀中,沪滨诸父老,犹道铁侯功”。
在民国时期,一件乌铜走银墨盒能够买到“实价壹佰廿元”(实价一百二十元),可抵一个一般的三口之家一年的开支,称其为奢华品亦不为过。
其实,不管是烟膏盒仍是墨盒,器型和用处的差异没办法掩盖其制造流程与工艺之精和艺术水准之高。彼时的乌铜走银真是风头无两,名望上“乌铜器举世闻名”,商场上“产品销路甚广,近销邻县、省、州,远至香港、国外”,在纯手工制造的条件下,乌铜走银的年产量竟能到达30005000件,其热度之高可见一斑。
清末时,乌铜走银就开端打破“始惟岳姓能制”的局势,开端从石屏向外地传达,呈现“能者日众,省市肆盛行”的局势,个旧、蒙自、东川、腾冲、昆明都开端出现制造乌铜走银的匠人,外姓人也开端把握乌铜走银制造技艺。
眼看闻名度和商场已翻开,一声炮响送走了乌铜走银的黄金时代。抗日战役后,时局动乱、物料紧缺,最炽热的岳氏店肆也开端惨淡。20世纪五六十时代,受战役重创影响,百废待兴的新我国开端清点资源,对贵金属进行统管,许多匠人纷繁转行,不再从事乌铜走银的手工出产,乌铜走银堕入全面衰落、接近失传的地步。
直至20世纪八九十时代,全国经济转型复苏后,乌铜走银开端在岳忠祥、金永才等民间艺人的研究下得以逢凶化吉。
石屏原是乌铜走银的故土,阅历全面停产的危机后简直隐姓埋名,岳忠祥为连续祖传手工,打破“传男不传女”的祖训,把乌铜走银技艺教授给女儿岳丽娟,父女俩在石屏兴办“云岳乌银工艺厂”,但因种种原因而关厂歇业。
金永才的师傅李加汝早年在昆明岳家店肆做学徒,后因战乱停艺多年,晚年无子的他在晚年时得到金永才的悉心照料,临终前将这门手工传给金永才。继承衣钵后,金永才刻苦研究,技冠群雄,成为乌铜走银仅有的国家级传承人。为了传艺和营生,他在昆明官渡古镇开办乌铜走银传习馆,先后兴办“金李记”“金大师”品牌,广收学徒,据守至今。
2011年,乌铜走银制造技艺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项本来接近消亡的传统手工就在国家力气介入、民间手工人的尽力下开端康复活力。来自石屏的李伟于2012年拜师金永才,学成后开办“石屏乌铜走银传习馆”,出走了一个世纪,乌铜走银又从头在故土生根。
虽然以“非遗”之名再度被看见、连续,但相较于其他商场化敏捷的传统手工艺而言,乌铜走银仍然步履维艰。现存的乌铜走银传习馆仅两家,独裁乌铜走银的店肆不过个位数,大多数乌铜走银手工人需求靠修复古器、打制银器等各种兼职才干养活自己和家人。
面临此情此景,八十多岁的金永才宣布慨叹:“真金白银卖不过泥巴。”他口中的泥巴,指的便是现在备受商场喜爱的各类闻名陶器。话虽直白,却道尽乌铜走银手工人的无法。
商场反应远不如同为“云南美器”的鹤庆银器和建水紫陶,闻名度更无法与繁复耀眼的景泰蓝混为一谈。无商场、无名望、无人才的“三无”乌铜走银若想康复民国时期的盛况,还需求穿行一段极为困难的路途。
遐想岳飞当年,面临金兀术的精锐金军,他勇猛直前、平定寇乱,因战功显赫而受全国奖励;面临“拥兵自重、妄图篡位”的奸佞谗言和漆黑政治斗争,他意志坚定、宁死不从,终究被赐死临安风云亭,“精忠报国”成千古绝字。
器物虽无言,但却和人相同,具有共同的生命进程和个性特征。乌铜走银在前史中跌宕起伏,从传奇面世到炙手可热,又急速下跌谷底、无人问津,再到现在的枯木逢春、山穷水尽。那些永不消逝的银纹持久地沉默着,兀自穿越前史,遥远地回应着岳飞的一清二楚、坚强不屈。
不管时局怎么改变,乌铜走银一直自我克制自重、历久弥新,青红皂白,都留予后人评说。待从头,拾掇旧山河,拂去从前鼎盛一时和近乎绝迹的“尘与土”,期望乌铜走银迎来归于本身个人的“云和月”。(本文系2024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普项目《小城大器:云南非遗美器》科普文章,作者:朱雨航)
搪瓷反应釜厂家澳客官网电脑版登录-彩票电脑app官方版下载,主要生产销售搪瓷反应釜、山东搪玻璃反应釜等产品,参数说明详细,,订购价格有优惠 网站地图